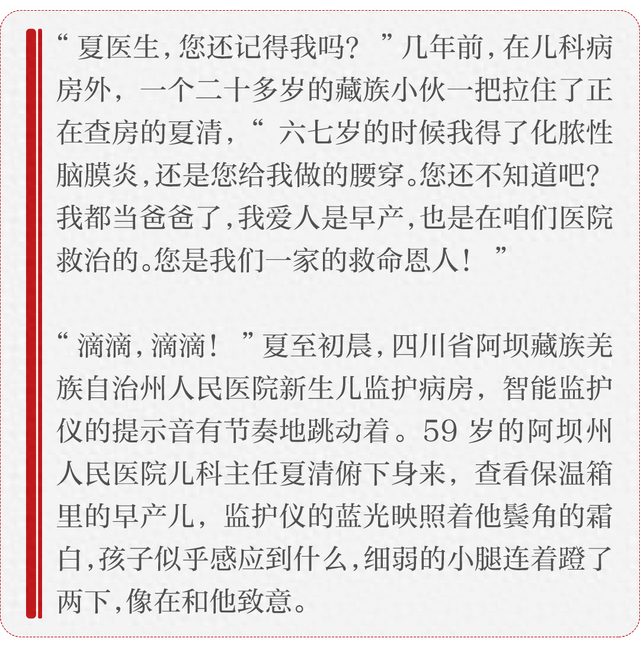
来看看这群孩子丰云股票,是夏清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,不知不觉就从青丝看到了白发。时光回溯至1988年,23岁的夏清第一次走进这间儿科病房时,桌子上只有一副听诊器、几瓶常用药,空荡荡的病床间回荡着患儿微弱的啼哭。那时,他常常要攥紧颤抖的双手,才能忍住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。
三十七年过去,那个面对濒死患儿手足无措的年轻医生,如今已成为用双臂托起无数新生命的“夏爷爷”,在这片雪域高原,为万千儿童筑起一道坚实的生命防线。

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夏清(右)和同事讨论病例。受访者供图
从“怕医生”到“好医生”
“又是一个脓毒血症患儿,拖得重了才到医院,县里做了紧急处理,然后送咱们这儿了。”听着年轻医生的汇报,夏清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
夏清介绍,“这个病是由感染引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,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,需及时治疗。过去因为家长不了解,再加上路途遥远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儿离开。”
“这个病要攻克循环的管理、呼吸的管理,还要做内循环的调整,我们也是土办法和洋办法一起上,最终才摸索出了如今这一套治疗规范,现在救治效果比以前好太多了。”聊起儿科的进展,夏清也不再紧绷。
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儿科专家,医院里认识他的人很多,每走几步就会听到一声“夏医生”,夏清总是礼貌点点头。他话不算太多,皱起眉头时略显严厉,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难得一见的好大夫。
“当大夫挺好。”夏清回忆,高考时,他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的状元,志愿表上填的是地质、石油,医学只是随手勾选。命运却将他推向了这条路——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儿科系的录取通知书,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1988年的夏天,23岁的夏清站在阿坝州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前,手中的听诊器仿佛有千钧重。这个从小害怕到医院缝针的男孩,如今竟成了一名医生。
“医学是帮助别人的事业。”这句话让他燃起了对医学的兴趣,从成绩倒数飞跃至名列前茅。毕业后,他来到阿坝州,面对的是刚成立3年、仅有3名医生的儿科。
病房简陋,设备稀缺,新生儿死亡率高达35%。值夜班时,遇到父母怀抱奄奄一息的孩子冲进诊室,年轻的夏清常常束手无策。“那种无力感,像刀子一样扎心。”
1989年的深夜,一个11岁的藏族女孩被送来时已嘴唇发绀,脚部浮肿。没有血氧仪,夏清和同事们只能翻阅着借来的一本《实用儿科学》,按心衰紧急处理。吸氧、镇静,注射强心针、利尿剂……一套抢救措施下来,女孩的呼吸逐渐平稳。
“那是我第一次独自救回重症患儿。”夏清说丰云股票,那次经历让他明白,医学是一个从理论转化实践的过程,必须接触大量的病例才能累积经验。而越是边远的山区,越缺经验丰富的医生。
面对一张张稚嫩的小脸,夏清决定,当地医疗条件有限,那就去学、去改变。

阿坝州人民医院儿科新生儿病房。受访者供图
“边远地区的疾病并不边远”
阿坝州的冬天,寒风能穿透厚厚的藏袍。比气候更严峻的,是医疗的“荒原”。
1998年,夏清成了儿科主任,那时加上他,科室一共只有4名医生。“很多人为了更好的发展,选择了走出去,但我觉得外面的医生那么多,不缺我这一个。”
“我还在重庆医科大学读书的时候,学校广场上开了一场宣讲会,请来了毕业后到新疆去的一个医生。他说了一句话,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:‘边远地区的疾病并不边远。’”回忆起这段经历,夏清害羞地笑了,“我觉得医生在边远地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,就这样留了下来。”
接下来的十余年中,夏清从未有一刻松懈,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科室的发展上。在他和科室同事的不懈努力下,2012年,儿科建立新生儿病房,由普通病房改建而来,当时只有5张病床、1台暖箱。
“儿科的发展,是科室里所有人的众志成城。”夏清回忆,那个时候,他们经常熬红双眼走出病房,但一看到病房外家长充满期待的眼光,没有任何一个人叫苦喊累,大家都想做得再多一点,再好一点。“有了病房还不够,医疗设备、急救技术这些都得跟上。”
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,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。20多年前,转运危重患儿到成都,需颠簸两三天山路。“很多孩子没能撑到,在救护车上就没了。”回想起那些转运途中停了呼吸的小孩,夏清声音低沉,痛苦令他下定了决心:“要把新生儿急救作为科室发展的重点方向。”
2008年开始,在医院大力培养人才的背景下,夏清引领团队积极求学,从华西医院到北京协和,笔记攒了一摞又一摞。“我们的底子薄、基础差,去进修的时候起初也忐忑,但听说了我们的情况,华西医院的专家们几乎是倾囊相授,后来还派了专家来到实地帮扶。”
2014年,为建设四川省民族地区重点专科,阿坝州人民医院儿科添置了呼吸机、监护仪等一批新设备,发展迎来新的飞跃。
“最近几年,愿意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,设备有了、技术跟上了、人也更有心气了。”夏清说,在全科室医护“熬更守夜”的努力下,改变已然发生——新生儿病房扩至20张床位,有创呼吸机、无创呼吸机、血气监护仪、多功能暖箱等高级生命支持设备陆续到位。
有了硬件支持,救治效果显著提升。数字见证奇迹:如今,阿坝州新生儿死亡率从35%降至不到千分之三,早产儿救治成功率接近全省水平。

阿坝州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夏清(左三)在阿坝州人民医院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查房。受访者供图
家喻户晓的“夏爷爷”
“夏医生,您还记得我吗?”
几年前,在儿科病房外,一个二十多岁的藏族小伙一把拉住了正在查房的夏清,红扑扑的脸上满是激动。夏清一时有些恍惚,没想起眼前的小伙是谁。
“六七岁的时候我得了化脓性脑膜炎,还是您给我做的腰穿,才救了我一条命。”小伙越说越感慨,迟迟没有松开夏清的手。
看着眼前壮实的小伙,夏清心里也是感触颇深,“他一说我就记起来了,这个技术不难,是医生的基本功,但是当地家长对这种治疗方式很抗拒,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沟通,最后他的父母才同意。”
“我现在一点事都没了,就在咱们市里上班。”听着小伙叙述着自己的生活近况,夏清不自觉地就舒展了眉头,“您还不知道吧?我都当爸爸了,我爱人当时早产,也是在咱们医院救治的。夏医生,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!”
37年光阴,曾经的青年医生已鬓角染霜,夏清成了无数当地孩子的“夏爷爷”。
“医学的进步,是一代代人的接力。”夏清常对年轻医生说。他严格查房,即兴提问,逼着他们深夜查资料;又亲手示范气管插管、搭建新生儿急救转运团队;带队跑遍全州13个县,组织培训基层医生。如今,他仍坚持每年夏天下乡,向藏族同胞讲解母乳喂养的重要性,在牧场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诊治结核病患儿。
采访中,夏清数次表示,“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情,儿科的今天,离不开华西等医院的帮扶、离不开医院领导的扶持、更离不开儿科同仁的坚守。”
2014年,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,阿坝州儿科质控中心成立。夏清也在努力推动各县儿科独立分科。在他的坚持下,阿坝州很多县都有了独立儿科,新生儿急救网络覆盖高原。
傍晚的高原,夕阳为雪山镀上金边。夏清站在窗前,望着远处。“我们和顶尖医院仍有差距,但至少现在的孩子不用经历我们当年的无奈。”他的白大褂被风吹起,在海拔3000米处无声飘扬。
盛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